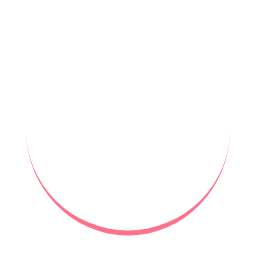我是一名在新加坡出生、香港成長的兒科醫生,正在南蘇丹戈格里亞勒,進行首次救援任務。
目前無國界醫生的醫院是整個戈格里亞勒地區唯一的醫療設施,提供緊急和婦產服務、兒科深切治療、兒科基層護理,以及為營養不良兒童而設的餵食治療中心。
南蘇丹是一個仍被內部衝突困擾的國家。在一連串複雜、甚至有時候暴力的社會、經濟、政治和地緣生存鏈當中,醫療問題顯而易見。要在這裡為這些身無長物──沒有食物、飲用水、教育、基建甚至安全──的人提供醫療護理,往往令人痛心。但我希望和你分享無國界醫生在這裡,以有限資源、創意和熱情所能做到的事。
非常感謝你有興趣,了解我們這場既富挑戰性又感性的旅程,也感謝你持續支持無國界醫生的工作!
同時感謝我的家人、朋友和香港瑪麗醫院的兒科隊伍(香港大學──我的家!),在過去數月給予我的支持和指導,為我帶來極大的幫助。
-------------------------------------
我站在朱巴灼熱的機場停機坪上,這裡是南蘇丹的首都,南蘇丹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板起臉,流著汗,我們是一群來自全球各個NGO的人道工作者,乘搭世界糧食計劃署的一架小貨機,前往這個國家各個角落完成項目。這是救援人員乘搭的唯一一種飛機,至於我們大箱的食物和醫療物資,都是由大型卡車運送的。
朱巴充當著無序的主要入口,讓數以萬計的人道工作者湧入這個世界上其中一個最貧窮的國家。飛機上擠滿了救援人員,彼此點了點頭,他們從巴黎、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和阿迪斯阿貝巴而來,可以從他們衣服和袋子上小小的紅色機構標誌辨認出來。他們並沒被朱巴機場四周的雜亂所干擾。「一旦你見識過南蘇丹,你什麼都見識過了。」一個荷蘭救援者低聲跟我說。
一排又一排白色高大的貨機醒目地印有聯合國、國際紅十字委員會、無國界醫生、世界宣明會和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標誌,在陽光下閃閃發光,一眼望去無邊無際。在高溫下,地平線搖曳著,把飛機映成熱帶草原上棕櫚樹的影子。但是,在這個青尼羅河與白尼羅河交接的國家,這不是海市蜃樓。偽裝部隊分散在飛機之間,蘇丹人民解放軍士兵靠著他們的坦克,扛著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警惕地打量著配裝線。敏感的安全區內禁止拍照,我的腦海裡馬上想到其他訪客在到達後因為拿出手機而被制止和詢問的故事。
在赤道上非洲灼熱的太陽高達攝氏50度,但困擾我的並不是臉上的汗。當我看到這裡殘酷的暴力,我熱淚盈眶,如此大的食物和救援需求讓人揪心。這是一個經過50年戰爭、取得獨立5年後,仍處於內戰和衝突中的國家。這是一個人們流離失所和忍受饑餓、1200萬人的生存無法獲得保障的國家。這是一個完全依賴於人道援助、沒有能力或實際資源去刺激獨立成長的國家。
我是一名出生在新加坡、在香港工作的兒科醫生,現在要去戈格里亞勒,即瓦拉普州的前省會,進行我第一個無國界醫生任務。這是位於西北部角落、靠近蘇丹邊界的偏遠地區。無國界醫生的飛機每月給我們運送一次藥物、醫療物資和食物補給。
我未來九個月的生活所需,都打包進兩個輕於25kg的背囊裡(這是人道救援的限制,因為行李重量要分配給醫療補給和食物)。所以很多被認為對我生存不必要的東西都被丟棄了。但這裡的人們拿著更少的東西,步行好幾天,擔驚害怕,僅僅為了尋找食物、水和安全。我小心翼翼地收拾心情,帶著更深的絕望,還有生命中的一切起伏來到這裡,但和這裡的人所經歷的比起來,只是小巫見大巫。
我花了10年時間讓自己有資格坐上這架飛機——努力地工作、經歷心痛、克服一個個障礙來實現夢想——但和這個國家的痛苦比起來不僅相形見絀,而且那痛苦在這裡放大了數十年。過了這麼久,我終於來到這裡,緩解了之前一切的個人考驗和磨難的記憶。我在這裡看到的一切,衝擊著我的人性與同情心,而我已開始承受著那些所帶來的餘震。
最初被埃及佔領,然後在殖民時期由英國和埃及共同治理,南蘇丹的領土和北蘇丹共和國在1956年取得獨立。然而,從英國獨立後,在北方佔大多數的穆斯林和在南方佔大多數的基督徒旋即爆發內戰,原因包括歷史上南方人的奴役問題(基督徒因此成為反對派,事件亦加深了民族認同)、深層次的民族和部落分歧,以及在邊境因自然資源和石油造成的紛爭。
在1955至1972年和1983至1972年兩場蘇丹內戰後,南蘇丹在2011年7月的全體公民投票中以98.83%支持率獲得獨立,然而在一個使用著超過60種不同部落語言的國家,儘管在2015年8月,總統SalvaKiir(丁卡族)和副總統 Riek Machar (努爾人部落)簽署了和平協定,但內部政治和種族暴力衝突持續不斷。這個國家政局緊張,人人屏息以待,因為經濟不穩定導致的高通脹,正在威脅這脆弱的停火狀態,把國家帶向動盪。
飛行前一晚,我躺在床上睡不著。在這首都城市,隨機的槍聲徹夜響起。我因為自己知識不足、無法盡力幫助遭受磨難的南蘇丹人民的恐懼而飽受折磨。我知道這裡看到的疾病、病人和醫療資源,和我們在家看到的截然不同,這讓我感到疲乏無力。
當我在第一世界的醫院待命,儘管有專家和專業的護理,我仍要每小時醒來檢查確認早產新生兒在深切治療室的情況,我以為這樣的失眠已夠糟了。我們觸碰他們小小的心臟,想像他們過早來到這個世界的感想,想像他們因我們而承受了多少痛苦,只是為了活下去。奇跡或會證明我們和科學都是錯的,迫使我們更殘酷地追求好的結果,但一切都沒有保證。生與死的迴圈,隨著時間、空間和經歷變化起伏。
但現在在這裡,要進行搶救的話,大概是徒勞的,因為沒有用於氣道插管的管子、沒有呼吸機、沒有特殊注射藥物來讓他們的心臟運作。沒有那些在任何其他地方都能夠提供、讓寶寶得到茁壯成長機會的資源和技術,我們要怎麼提供最佳的醫療護理?
在什麼情況下,一個醫生會放棄寶寶?
最終令人心碎的是,無論你做什麼,都會讓他們失望,因為現在戈格里亞勒是一個相對無衝突地區,在有限的資源下,我們必須關閉項目,將我們的焦點放到其他項目上。無國界醫生是一個緊急救援組織。危機管理(不是發展)一直是我們的使命。但在戈格里亞勒幾乎沒有其他非政府組織在做長期的項目。未來模糊不清。我們走了以後,誰還會在這裡呢?我們能找到其他人來接管這個項目嗎?
飛機在大片的紅泥地和無人居住的乾旱沙漠灌木林上翱翔。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多明尼加農業學家,他指著遠處小村莊,那裡有簡單但古雅的茅屋,和用茅草鋪蓋的屋頂。巨大的棕櫚樹,長著成熟沉甸甸的黃色果實,向著非洲的陽光伸展著他們僵硬的綠手指。雨季後這真是一片良田,他說。他告訴我他是如何教在Rumbekto的小社區種芝麻和秋葵,以及向他們展示怎樣用一頭牛去拉犁翻土,而不是只把牲畜當成傳統聘禮。他解釋非政府組織如何鑽孔打洞以拿取在地下4米的水來灌溉田地。我們滑翔著,穿過平流層,在這個破碎國家的上空,他則用沙啞的聲音拼湊著樂觀的碎片。
著陸時,下降帶來熾熱的衝擊,我們有默契地抓緊了彼此的手。我把沉重背包扛在肩上,開始漫長而孤獨的行走,穿過另一英里、滿是救援組織飛機的著陸跑道。南蘇丹在蹂躪著它自己。掙扎了這麼久後終於來到這片野蠻和人性共存之地,我的存在僅僅提醒著這裡還未被照顧到的巨大需求。
我想到年邁而非常擔憂的父母,看著我要離家,前來這個他們永遠不會理解的世界。道別的時候,他們無助地轉開哭泣的臉,媽媽緊緊抓著父親微曲的背部作依靠。他們唯一的女兒,得到了所有可以實現亞洲人眼中成功和發展價值的機會,被養成符合亞洲人端莊有禮的特質,現在卻要飛到一個內戰國家。
我很感謝能有這麼一個在無國界醫生工作機會,讓我能謙卑並挑戰自己,讓我可以跟隨自己的內心,看著它徹底粉碎,並選擇成長......這是我做過最自私的事情。每一步,我都吞下驚愕、恐懼和內疚的種子,感受著一生中前所未有的孤獨和迷失。
這裡沒有真正的客運站,只有一個人聲喧鬧倒坍了的小棲息處。他們告訴我,要去找一個穿著無國界醫生外套的人。傑米,我們的司機在塵霧中出現,他舒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微笑和步態,大手握著我的小手。他六尺四吋的高挑身材明顯比我高很多,看著我把頭仰後才能看到他的臉,向他道謝,他便眯著眼露出燦爛的笑容。
在4小時的車程中,他總是喋喋不休,教我丁卡語的生字(這個州絕大多數人使用的方言),給我講之前來自世界各地的國際醫護人員的故事,以及他們所分享的各國風俗來逗我開心。阿拉伯文的指示牌仍舊無處不在,提醒著往事。來自收音機不搭調的阿拉伯音樂節奏,配合著越野車在每個坑窪上的起伏,車子與沒有鋪好的泥路摩擦著。「雨水和泥土襲來的時候,人們哪裡都去不了,」他嚴肅地告訴我:「連救護車也過不了。」
我們停在一個路邊攤,穿著五彩繽紛像霓虹一樣長袍的婦女,給我們遞上裝滿整個大啤酒杯的香甜芒果汁。瘦得可怕的小孩圍到車邊,驚奇地用手指按在我們車窗上,喊著:「Kawaja(白人)! !」但同樣地,許多營養不良的婦女穿著破爛的衣服,蒼蠅圍繞著他們懷抱著的瘦骨嶙峋的羸弱嬰兒,他們向我伸來乾癟的手,掌心向上,向我求助。一些人從小縫隙伸手來,拼命地抓住我的衣服。有些患有白內障失明、沒有接受治療的男子,踉踉蹌蹌虛弱地走過市集。在簡陋的手推車上,癱瘓和截肢的少年向我們呼喊。「我們不能把錢給他們。」傑米對我說,並趕走了他們。我的手放在口袋裡,甚至拿不出什麼東西來幫上忙。
當我們的車開過那些被大火夷為平地的村莊,殘餘的木頭和稻草飄散在風中,他露出黯淡進而憤怒的目光,嘴唇壓成一條細線,他緊緊地握著方向盤,手指關節都發白了。
「你的國家是什麼樣子的?」他問我:「你的家是怎樣的?」
我猶豫了片刻,想起我們的摩天大樓,多元種族在疏離但和諧的空間下共存,豐富的食物伴隨著大量浪費。
他關了收音機,向我們四周荒涼的草地揮手,當敵人來襲擊時,人們就會跑來,躲進這片灌木林裡。他們過去常在沼澤深及頸項的地方隱藏個幾天。可是上年的雨季來晚了,現在包括河流在內,幾乎所有的水源都蒸發掉了。光禿禿的樹木把它白色的枝幹伸向四方八面,一次又一次插入黏土,它的根不斷尋找水份。我們離蘇丹邊境如此地近,這是繼利比亞沙漠,世界上第二熱的國家,白天最高溫可到攝氏50至55度。枯瘦如柴的人在巨大的芒果樹下,憔悴疲憊像成堆的白骨,暫時緩解饑餓和悶熱。
「那裡有戰爭嗎?」他用強硬的口氣問道。「你的人民會殺害他們的親兄弟嗎?」
我看著赤腳的南蘇丹男人、女人和小孩赤腳走在路上那火柴似的倒影,當我們的貨車經過,怪異的滾滾褐色煙霧時隱時現。就在一年前,有意進行恐怖可怕屠殺的敵人部落在這塵土飛揚的道路上出現。在全國各地,人們每天疲於逃命,沒有財產、水或食物,只是為了去某個地方。這些人可能在去我們醫院的途中,它是這整個地區唯一的一間醫院,但我們不能停下來接載他們。我們要遵守安全指引,而且有些十幾歲的男孩還穿著大號的制服,嚇唬晃動著他們的步槍。孩子們穿著二手衣服,可怕地玩著角色模擬遊戲,這裡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在戰爭的遊戲中長大。
「不。」我小聲地說道。「不像這樣。但我們很幸運,擁有多年的和平。」
「這裡不會有和平的,」他告訴我。「我們不是農民,我們不會等待季節變更,雨水到來。我們是戰士,堅硬土地上堅強的人。我們通過戰鬥去拿到我們想要的和我們應得的。一直都是這樣,以後也會這樣,這就是我們的生存之道。我們準備好去戰鬥,迎接死亡,人命毫無意義。」
我把我的嘴唇咬出血了,令人窒息的血紅色的灰塵鑽進我的肺部,兩額感受著自己的心跳。我們安靜地趕路,直到到達無國界醫生的標識。
「我們到了。」他喘著氣,把我從越野車上把我接下來。
在一棵巨大的金合歡樹下,背後映襯著紫粉紅色的日落光線,無國界醫生國際團隊正在進行一個醫療會議。當我被領到座位上,接過對講機,一張張燦爛的笑臉都轉向我。我們討論感染控制、服務品質及該如何改善,未來人類和醫療資源的挑戰,以及未來幾個月人員培訓的計畫。
細心縝密的戰略制定和樂觀熱情帶動著討論。一整天沉重不安的心終於安定下來。
「歡迎來到無國界醫生組織戈格里亞勒樂園,」另一個醫生沖我眨眨眼睛。「歡迎回家。」
免責聲明:以上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及經歷。如有雷同,實屬巧合。為保護隱私,涉及名字已作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