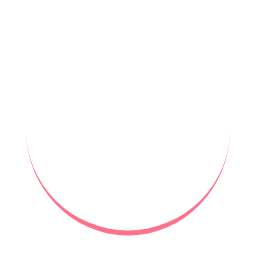2017年,超過70萬羅興亞人為躲避緬甸軍方針對性的極端暴力而來到孟加拉。阿敏 (Ruhul Amin) 是羅興亞人,傑根 (Arunn Jegan)來自澳洲,他們正於八年前在當地相識,是無國界醫生的同事。多年來,兩人多次合作參與各個項目,不斷挑戰提供援助的種種界限。
八年過去,孟加拉的各個難民營已擴展至容納超過130萬羅興亞難民在內,棲身其中的人前景極不明朗。在庫圖巴朗難民營狹小的空間裏,10位羅興亞藝術家與10名兒童攜手創作,以芋葉為象徵,用新方式訴說著羅興亞人無國籍的故事。阿敏和傑根均參與其中,這段對話記錄了他們的創意合作與日益深厚的友誼。
傑根:我初次見到阿敏時,他和家人剛剛越過邊境進入孟加拉,身無長物。我當時並不認識他,但當他告訴我他曾在緬甸為無國界醫生工作,我感到很親切。聽到他失去一切的遭遇令人心碎。我給他指示到辦公室的方向,說可以到那邊領取工資,他說他需要取水,我們就分道揚鑣了。
阿敏:我當時還沒看清傑根,只見一個皮膚黝黑的男人,說他住在澳洲。我不記得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是泰米爾人——其族群同樣遭受過暴行。我腦中只想着生存:今晚睡哪兒?怎樣找食物?我筋疲力盡,感覺自己像海上漂浮,不知何去何從。我以為很快會回家,卻沒想到8年後,我依然無法回到我的祖國。
這短暫的交流開啟了一段持久的夥伴關係。二人曾一起參與多個緊急應對和長期的人道項目。但他們始終沒有忘記一個問題:何謂提供護理?醫療護理固然重要,但生存並不等同於生活,而羅興亞人兩方面都舉步維艱。
阿敏:2017年,羅興亞人大批逃離緬甸後,無國界醫生是首批在新建的難民營中開展工作的非政府組織之一。我們在兩周內就建立了一個醫護人員社區網路。我們的工作很簡單:將病人送到醫院,並告知人們如何尋求醫療援助。當時不少人身上有槍傷、刀傷,還有未經治療的感染。營內沒有廁所、棲身處,也沒有道路。我記得有三個女人昏迷倒在泥地,身上滿是蒼蠅。我自掏荷包付了600塔卡(約48港元)給社區成員,把她們送到無國界醫生的醫院。我們只有人力救護車——用竹擔架或者直接背著病人前往醫院。
傑根:那場面很震撼,也令我想起了自己社群曾經歷流離失所——成千上萬家庭攜帶僅有的家當逃離;許多人身受槍傷;衣服上還殘留着硝煙的味道;混亂中失散的家人焦急地尋找孩子。我們在六周內建起醫院,幾天內建起水泵。幾乎沒有時間停下來感受任何情緒。
阿敏:我記得當時心中有種特別的感受。多年後再次見到傑根時,我才明白是人與人之間隨時間累積而成的連結力量。
幾年過去了,難民營的需求也隨之改變。昔日在緬甸遭受的槍傷,變成長期醫療狀況;白喉、疥瘡和丙型肝炎的大規模流行病疫情迅速失控蔓延,對社區健康構成嚴峻威脅。羅興亞人面臨難民生活帶來的新挑戰。
雖然基礎設施有所改善,但對未來的希望卻日漸黯淡。2019冠收病毒病疫情和圍堵政策帶來了行動管制和鐵絲網圍欄,援助資源亦逐步減少。如今,這難民營收容了超過130萬羅興亞難民,有些已在此生活數十年,有些則僅落腳數月,而營地已淪為了用竹材和防水布搭建成的貧民窟。在這片未知的混沌之中,有嬰兒誕生,也有人在漂泊不定中變老。
阿敏和傑根現在不禁要問:當援助資金枯竭,當一個人的法律身分40年來未曾改變,人們要靠甚麼維持生活?無國籍的狀態到底意味着甚麼?對於那些和他們並肩奮鬥的人來又代表甚麼意思?
傑根:2019年,我再次見到阿敏。那次重逢讓我感到我倆的聯繫更緊密了。他曾告訴我,他花了4年時間才感到足夠安全向我坦白無國籍的真正意義。
阿敏:我從不稱呼自己是「無國籍」,我稱之為「活着」。我沒指望過能接受教育,也沒想過能獲得醫療或遷徙自由。我以為教育和機會只屬於某些人。我們對生活可能性的想像非常狹隘。直到離開祖國,我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被剝奪了多少權利。這種覺悟令人痛苦。它不僅傷害你的身體,也會刺痛心靈。
這次見面對談孕育出一個新意念。如果醫療援助是為了治癒身體,那麼甚麼能治癒我們的內心,讓我們不再懷疑自己是否重要?他們著手創建一個植根於人們存在、文化和故事的項目,幫助羅興亞人表達自己,抵抗被抹除的待遇,並且與他們的身分保持連結。他們找來了一群理念相近的澳洲和羅興亞藝術家、一成了創意倡議合作夥伴。
阿敏:我們的工作坊裏,一個象徵逐漸浮現——芋頭葉。靈感來自一句羅興亞諺語,意思是:「水滴芋頭葉,風吹了無痕。」( Hoñsu Fathar Faaní)
傑根:芋葉蠟質似的表面有會讓水珠滾落而不留痕跡。
阿敏:這象徵着世界如何讓羅興亞人失去國籍,並試圖抹去我們存在的一切印記。但我們依然在此,並留下羅興亞人活着的印記。
傑根:羅興亞的成人、兒童和藝術家親手製作他們心中的芋頭葉。看到人們通過創造力蛻變,令人感觸良多。一位羅興亞陶藝師告訴我們,他的家園8年前被毀,但他直到最近才逃離。那種緩慢消亡的壓力令人窒息。然而,在這個共用的空間裏,人們開始敞開心扉,甚至宗教和民族認同之間的緊張關係也逐漸緩和。這就是共同創造的力量。
阿敏:但這不僅僅是為了表達自我,更是為了生存。救援組織終會離開,援助資金也會用盡。我們不願餘生都依賴援助組織,依靠他人讓我們深感羞恥。我們只要與自己的文化、身分認同和社群保持連結,我們就能繼續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連結,是治癒心靈的最佳良藥。
傑根:阿敏告訴我,他感覺內心的光芒黯淡起來。這並不是因為他放棄了,而是因為與外界隔絕的重壓越來越強——行動受限、護理從缺、機會渺茫。我聽到「命運」和「天數」的次數遠多於「希望」和「未來」。
阿敏:我不是營地裏唯一有這感受的人。對我們來說,這個項目不是業餘活動,而是一種延續內心光芒的方式。我們仍然面臨巨大的健康挑戰,糧食配給被削減,原因不明的發燒,以及惡劣的生活條件。美國國際開發署和英國的資金削減正令我們的未來岌岌可危——許多醫療中心已經關閉。就連我的兒子需要緊急護理時也沒有人承擔手術費用。
傑根:這並非要以創意倡議取代醫療援助,而是認清若缺少其中任何一環,一個族群將迅速變得面目模糊。。整體護理的理念不僅提供潔淨的繃帶或營養配給,更是認同人類對認同感、情感連結和歸屬感的內在需求,這正是人道工作未來必須抵達的方向。
阿敏:在一個連國籍、行動自由甚至醫療護理都被剝奪的地方,捏陶土、做竹編、講故事這些簡單的舉動,都成了捍衛尊嚴的抵抗,訴說着:我們依然存在,我們依然能感受,我們依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