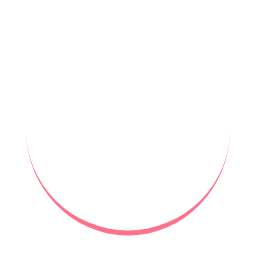作為無國界醫生的醫生,我曾參與15次醫療撤離行動,協助病人從加沙撤離,途經埃及與約旦,再轉送到其他國家。而無國界醫生作為促成瑞士和歐盟當局經約旦作醫療撤離的合作夥伴,已參與安排病人前往瑞士、愛爾蘭、英國和西班牙。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登記紀錄,目前有16,500名病人正等待醫療撤離,但這僅是滄海一粟,仍有更多病人亟需撤離。名單上約半數病人是種族滅絕與轟炸的受害者,身負嚴重骨折、燒傷、脊椎損傷、截肢,且幾乎無法獲得復康治療。其他病人則患有先天疾病或心血管疾病,因治療延誤而病情惡化。饑餓與延遲護理使他們的狀況日益轉壞。
陪同病人前往瑞士,讓我清楚看見他們正面對的艱難處境。這一輪撤離共有13名兒童及其家屬。他們筋疲力盡、飽受創傷,擔心留在加沙的親人安危。有一幕令我印象尤其深刻。在安曼的阿麗亞王后(Queen Alia)國際機場,一名旅客牽着狗經過,母親們便輕聲說:「看,連這隻狗都有護照,可以到處旅行,而我們卻不能。」她們表面上笑着,但這話道出了巴勒斯坦人長年所承受的不公與非人道對待。
停留安曼期間,他們每天獲得三餐,對我們而言是再平常不過的事,但對他們卻是難以置信的體驗,這讓我意識到他們的營養不良程度。許多人甚至因身體長期缺乏營養、未能適應正常營養汲取而出現腸胃炎。在加沙,他們連每天只能一餐也不容易做到。
撤離過程本身既複雜又令人沮喪,許多急症病人往往在等待中死去。我記得我們的同事卡拉達亞(Abed El Hameed Qaradaya),他在加沙遭以色列襲擊受傷,當時還有其他人受傷,我們的同事哈耶克(Omar Hayek)也當場身亡。
卡拉達亞傷勢危重,急需手術,但在加沙無法進行。我們嘗試撤離他,但他在等候許可的兩天內去世。如果能及時獲得適當治療,他本可存活。我能想像有多少病人像他一樣在等待之中死去。官方數據顯示,約900名登記撤離的病人在獲准前已離世,而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另一個挑戰是目的地國家有限,願意接收加沙病人的國家非常少,且往往設下嚴格的「條件清單」。此外,這些國家通常優先接收兒童,但兒童僅佔所有個案約25%。成人與長者經常被拒絕撤離,而繁瑣的文件、安檢及醫療審批更進一步延誤。
每天,我們都在見證其人命代價。看着病人在等待撤離時死去,是最令人心碎的感覺。然而,也有些微小的瞬間,深深烙印在我心中,悲傷與欣慰交織。在另一趟從安曼出發的撤離中,我們與幾名孩子同乘救護車,途中,一名孩子突然興奮尖叫,因為他看見一間賣巴克拉瓦(baklava,一種酥皮甜點)的甜品店。我請他們進店裏,孩子們立刻奔跑進去,其中一個男孩馬上以視訊致電仍在加沙的父親,給他一一展示店裏的甜點。父親凝視着螢幕上的巴克拉瓦,眼神中滿是深深的渴望,那一刻,我多麼希望能把這些甜點帶給他。
孩子們欣喜若狂,笑聲不斷,急切挑選甜點,並反覆說他們已兩年沒吃過巴克拉瓦。這是一個微小卻深刻的提醒:他們失去的不只是食物,還有童年的最簡單的快樂。
我本身是巴勒斯坦人,父母來自加沙,我仍有家人留在當地,但我一生從未能探望他們。目睹人們承受難以想像的苦難,令我心痛不已。更痛苦的是,當我聽到有人說:「加沙不是停火了嗎?為甚麼不能在當地接受治療?」事實是,逃離加沙的人並非出於選擇,而是為了生存。
加沙的醫療系統已崩潰,醫院被摧毀,醫護人員流離失所,醫療物資極度匱乏。許多病人需要當地無法提供的治療,在醫療系統能重建好之前,醫療撤離就是唯一能救命的方法。儘管所謂的停火生效中,人們仍在武裝襲擊中喪命。
我還常聽到另一種說法:「你們為何要掏空加沙的人口?」我需強調,醫療撤離並非鼓勵移民,病人保有返回加沙的權利,治療完成後可回到家園。我們會向病人及家屬保證,當後續護理及藥物供應穩定時,他們有權返回加沙。
在這份工作中,每一天都帶來新的故事——關於苦難,也關於堅韌與希望。作為醫生與人道工作者,看着病人因等待撤離而死去,心碎得難以言喻。但每一個被救回的生命、每一個能再次品嚐吃甜點、玩耍、康復的孩子,都讓這份工作更顯深刻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