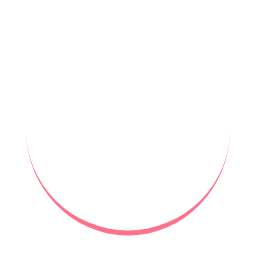自2011年利比亞政府倒台以來,該國陷入嚴重分裂。移民與難民經常成為武裝組織、人口販運集團及國家部門的目標。利比亞法律將所有非正規移民視為非法,不區分尋求庇護者、人口販賣受害者或其他弱勢人士。
這種法律真空導致大規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性暴力及強迫勞動。許多人在海上被攔截後被強行遣返利比亞,再陷暴力循環。
2024年,無國界醫生展開《流離之人》項目,從多名移民、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的證詞中,精選出400個故事,並透過藝術形式呈現,藉此紀錄、倡議及發聲。
展覽中的400幅畫作由四名藝術家所創作,他們為每段難民的經歷賦予面孔與生命。作品生動地呈現了人們在逃亡過程中的種種經歷,包括綁架、性暴力與身體虐待,同時也彰顯了他們的堅韌與勇敢。每一張臉孔,都代表一個應被尊重與守護的生命。
《流離之人》是一場由難民主導的集體敘事行動。完整展覽現已於網上展出,以下為八個精選故事與作品。
32歲婦女,來自摩洛哥|2017年從搜救船上獲得的證詞
 我於2009年搬到利比亞,在扎維亞(Zawiya)的姐姐協助安頓,幫我找到住處和工作。我先擔任家庭傭工四年,後來轉到一間酒吧工作。
我於2009年搬到利比亞,在扎維亞(Zawiya)的姐姐協助安頓,幫我找到住處和工作。我先擔任家庭傭工四年,後來轉到一間酒吧工作。
2013年,我遭一個幫派綁架。在接下來的一周內,我每天都遭20名男子輪暴,幾乎喪命。最終,他們將我棄於街頭。那七個月裏,我幾乎與世隔絕,除了姐姐沒再見過任何人。
當我終於鼓起勇氣再次外出時,又被另一幫派綁架。他們把我帶到一處農場,在那裏我再次每天遭數名男子強暴,直至他們將我棄於街頭。
2015年,我嫁給了一個男人。起初他對我很好,但當我懷孕後,他毆打我的腹部直至我流產。上個月,我發現自己再次懷孕,於是逃離並藏身於朋友家中。
藝術家:Souad Kokash
18歲少女,來自尼日利亞|2016年於一艘搜救船上提供的證詞

我父親強迫我嫁給一名他欠債的男子,但母親拒絕了這門婚事,於是父親便說我必須離開家。
我和朋友一同去到貝寧(Benin)市,在那裏我們遇到一名男子,他聲稱可以帶我們前往歐洲,從事高薪工作。但到了利比亞,他卻將我們帶到一間妓院。我拒絕從事性工作,他們便讓我挨餓,每天毆打我。最終,我被迫屈服。起初我流了很多血,需要接受治療,他們說會把費用加到聲稱我所欠的錢上。
我曾試圖逃跑,但被抓回並遭到毒打。我也曾多次被阿拉伯人綁架,他們用槍打我,並強暴我。最終,我成功逃脫。一名阿拉伯人伸出援手——他將我送往薩布拉塔(Subratha),並為我支付由地中海前往歐洲的費用。
藝術家:Souad Kokash
35歲男人,來自孟加拉|2017年於利比亞提供證詞
 一名中間人遊說我前往利比亞工作,聲稱當地經濟蓬勃發展。他開價80萬塔卡(約5萬港元),但我們無力負擔。他同意先收取20萬塔卡(約1.3萬港元,餘額由他安排。
一名中間人遊說我前往利比亞工作,聲稱當地經濟蓬勃發展。他開價80萬塔卡(約5萬港元),但我們無力負擔。他同意先收取20萬塔卡(約1.3萬港元,餘額由他安排。
抵達的黎波里後,幾名利比亞人將我與另外11人一同載往一間屋子,車窗全被遮掩。他們強迫我致電家人付錢予那名中間人。當我以為接下來會獲得工作機會,但卻沒有。
其後,我在街上被警察截查。他們對我施以暴力,搶走了我所有錢和手機。
後來,我遇到一位孟加拉人可以幫我安排偷渡。但登船前,我被關在一間房內整整兩個星期,幾乎沒有水和食物。這段經歷令我精神受創。
藝術家:Tawab Safi
16歲少年,來自厄立特里亞|2021年於利比亞提供證詞
 去年二月我來到利比亞,被關在拜尼沃利德(Bani Walid),後來轉送到的黎波里的古特沙勒(Ghut Shaal)入境拘留中心。那是我去過最惡劣的地方,一個只能容納50人的房間擠了400人,沒有窗戶,每次守衞開門時都有人暈倒。
去年二月我來到利比亞,被關在拜尼沃利德(Bani Walid),後來轉送到的黎波里的古特沙勒(Ghut Shaal)入境拘留中心。那是我去過最惡劣的地方,一個只能容納50人的房間擠了400人,沒有窗戶,每次守衞開門時都有人暈倒。
食物令人作嘔,我們認為他們在食物裏加了安眠藥。然而,最令人恐懼的,莫過於那些與守衞合作的在囚人士。他們不但對我們施以酷刑,還會向守衞報告牢房內的一切動靜,例如我們曾試圖以湯匙鑿牆逃走的事。
有一次,他們說要遣送蘇丹人,我便假扮成蘇丹人,才得以從拘留中心逃脫。自此,我一直流落,沒有工作和分毫收入,也沒有糧食。
藝術家:Tawab Safi
27歲婦女,來自尼日利亞|2016年於一艘搜救船上提供的證詞
 我離開家鄉,因村裏的人打算對我女兒施行女性割禮(FGM)。我與朋友艾拉(Ella)逃往另一個村莊。起初一切都很好,我們各自找到工作—我當髮型師,艾拉則在銀行任職。然而不久後,艾拉的叔叔決定將她嫁給一名年長的朋友。他們把她鎖起來,直到能安排婚禮。
我離開家鄉,因村裏的人打算對我女兒施行女性割禮(FGM)。我與朋友艾拉(Ella)逃往另一個村莊。起初一切都很好,我們各自找到工作—我當髮型師,艾拉則在銀行任職。然而不久後,艾拉的叔叔決定將她嫁給一名年長的朋友。他們把她鎖起來,直到能安排婚禮。
有一晚,我們設法逃了出來。我們聽說在利比亞有工作機會,卻最終落入陷阱,被囚禁在一間屋內。他們企圖強迫我們從事性工作,我們拒絕後便遭到毆打。某晚,他們突然放我們離開。我們被夾在一大群人中,被驅趕至海邊。我一度以為他們要殺了我們,但他們卻將我們趕到一艘橡皮艇。沒有人問過我們是否願意離開。我們並非自願來到這裏,可是如今已無法回頭。
藝術家:Barly Tshibanda
28歲婦女,來自尼日利亞|2016年於一艘搜救船上提供的證詞
 我永遠不會結婚。我對男性毫無浪漫幻想,因為我所有的經歷都充滿痛苦與暴力。我在極度創傷中失去了童貞,青少年時期曾遭性侵——而這僅僅是噩夢的開始。
我永遠不會結婚。我對男性毫無浪漫幻想,因為我所有的經歷都充滿痛苦與暴力。我在極度創傷中失去了童貞,青少年時期曾遭性侵——而這僅僅是噩夢的開始。
我原本獲得大學醫學院的錄取資格,但因姐姐的男朋友承諾我在利比亞可以賺到更多錢,我最終放棄了學業。抵達當地後,我才驚覺他竟企圖讓我從事性工作。當我拒絕時,他便讓我挨餓,並用皮帶毒打我。最終,我被迫妥協,開始接待他眾多的客人。有一天,七名男子闖入並輪暴我——他們是為了報復,因為他曾開槍打傷他人。我在醫院住了兩個月,在朋友照料下康復。經過多次嘗試,我終於登上一艘前往歐洲的小船。
藝術品:Barly Tshibanda
55歲男人,來自巴基斯坦|2017年於一艘搜救船上提供的證詞

我曾在聯合國的免疫計劃工作,為阿富汗邊境山區的兒童接種小兒麻痺疫苗。但當地有人誤以為這項計劃是為了讓孩子失去生育能力,為此威脅要殺害我的家人。為逃離這些威脅,我決意離開,飛往的黎波里。抵達後,我開始從事勞動工作,以供養在家鄉的家人。但有一次,我遭到綁架,所有積蓄都被搶走。
我們坐船時遇到利比亞海岸衛隊。兩名持槍人員跳上船,搶走我們的金錢和手機,然後將我們丟在利比亞領海的邊界。接着另一艘船靠近,更奪去我們的摩打。
現在,我希望能申請庇護,盼有天能將家人接來與我團聚,因為巴基斯坦的情況實在艱難。
藝術家:Ngadi Smart
25歲婦女,來自科特迪瓦|2017年從搜救船上獲得的證詞

我與另外八名女性被關在一間小屋。趁夜裏沒有守衞時,我們會偷偷外出尋找食物——街上的一塊麵包,或任何能果腹的東西。
有一晚,一群阿拉伯人將我們帶到一間屋子裏,綁住我們的腿並強暴我們。我們也遭到毆打。即使他們鬆綁後,我仍無法走路。第二晚,他們再次施暴我們施暴,其後我們設法逃回小屋。
我已記不清我們在那裏待了多久。有一晚,幾名武裝男子蒙住我們的眼睛,把我們帶到薩布拉塔(Sabratha)的一個倉庫。隔天,他們用橡膠管打我們,兩名女孩當場死亡。有時我們兩三天得不到任何食物。
最終,我們被帶到海邊。我們驚恐萬分,因此再遭毆打,但最後他們還是把我們推上了一艘小船。
我現在懷孕了,我該怎辦?
藝術家:Ngadi Smart
由2016年至2023年,無國界醫生在利比亞提供醫療和人道援助,包括醫療護理、心理健康護理、轉介危重病人到專科醫療設施以及協助被任意拘留的人獲保護服務,他們往往在暴力和非人道的情況下被拘留在的黎波里各地的拘留中心。組織自2015年起便在地中海中部地區展開搜救行動,曾先後在八艘不同的搜索救援船上工作,拯救共94,000人。2024年12月,組織被迫停止最新一搜救船Geo Barents的運作,但承諾將重返地中海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