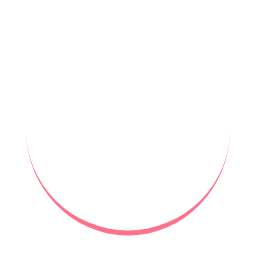我學會把人道放在首位。這也是我給我孩子的教誨。
安多高
驅使我的是「 病人永遠放置首位」這事實。身為醫學生,我早已知道這一點,但是與無國界醫生工作進一步鞏固這一點。與無國界醫生工作的短短幾個月裏,讓我有置身在家的感覺,更可以說我找到家人。
2001年,我開始在塞拉利昂南部省的莫揚巴(Moyamba)區為無國界醫生工作,當時正值內戰(1991-2002年)。雖然武裝衝突仍在持續,但局勢已開始趨於平靜,我們都期盼戰爭早日結束。我出生在莫揚巴區的邦巴馬 (Gbangbama)村,無國界醫生在我家的省份展開工作,所以我早已對他們有所了解。當時我剛從護理學校畢業,迫不及待想開始工作。當時無國界醫生在莫揚巴政府醫院為兒童、哺乳期母親和孕婦提供護理。我開始當一名護士,幾個月後成為了護士隊主管。
2002年,我搬到了通克利利(Tonkolili)區,無國界醫生當時正在那裏支援馬布拉卡政府醫院。我首次在兒科病房工作,在那裏我真正愛上我的工作。那段經驗讓我對工作有了新的目標感。我是一位父親,當我照顧病房裏的孩子時,我經常感到像照顧自己的孩子一樣。我在醫院治理過很多孩子。事實上,其中兩名現在是衞生部的護士。看到他們,我深感自豪。
2006年,我重返大學為成為社區健康人員作準備。為了繳學費,我賣過柴火,做過農務。畢業後,我在衞生部工作,在北部省的卡巴拉(Kabala)鎮展開疫苗接種運動,主要針對黃熱病、麻疹和小兒麻痺。之後我搬到了博城(Bo),而無國界醫生在那裏的貢達馬 轉介中心(Gondama referral centre )為15歲以下兒童和孕婦提供醫療護理。我當時擔任診所主管,以及同年稍後擔任數據編碼員。
應對出血熱(Hemorrhagic fevers)一直是我這些年來工作中最具挑戰的範疇。 2010年,我與無國界醫生在博城應對拉沙熱 (Lassa fever)。當時,我是唯一一名願意在病房工作的社區健康人員。我們團隊很小,只有一名醫生、幾名護士和我。大多數人都很害怕,但因為我想拯救生命所以加入。我曾經是拉沙熱病人,也曾有同事死於拉沙熱。我深知人們害怕靠近自己而感到被孤立、得不到妥善照顧的滋味。
2014年塞拉利昂爆發伊波拉疫情後,我從照顧拉沙熱病人轉為照顧伊波拉病人。當時伊波拉病毒對我們來說是新事物。很多人對它究竟是甚麼、從何而來感到困惑。由於每個人都急於尋找答案,當地開始上演一場互相指責的遊戲。在那段時間從事醫療工作需要勇氣。許多組織,包括無國界醫生,都在塞拉利昂展開應對來支援抗疫。身為醫護人員,我們必須盡自己的一份力量,阻止病毒傳播及治理病人。我的母親在這段時間經常打電話給我,嚷我在這段時間不要工作。她害怕失去她的長子,而我總是對她說 :「nya longoh ngie kpomiweh」 ,即「我必須幫忙」的意思。她過去從不理解我為何要這麼做,但她現稱我為「一名戰士」。
這些年來,每天穿戴個人防護裝備甚具挑戰,尤其是在炎熱乾旱天氣期間。有些日子簡直難以忍受,但我們互相提醒——我們也要保護自己。
2015 年宣布伊波拉疫情結束後,我回到馬布拉卡政府醫院工作,再次為無國界醫生工作,但這次是在兒童深切治療部。
我今年年底就要退休,以後會開始從事園藝。這些年來,我真的享受在無國界醫生的工作。無國界醫生教我以人道為先,無私為本。這是我不會忘記的教訓,我也會這樣教導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