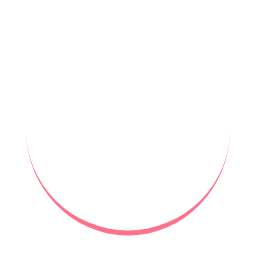撫平精神創傷 為無聲者吶喊
總幹事的話
撫平精神創傷 為無聲者吶喊
讀醫以前,我攻讀了心理學學士學位,過程中我逐步建立當醫生的原則──人們不只需要醫生護士等護人員去醫治他們肉體上的病痛,他們心理上的創傷同樣需要獲得關注。無國界醫生提供的精神健康支援,以及相關服務在人道危機中的重要性,正是今期《無疆》的主題。
在過去我曾參與的無國界醫生前線救援項目中,很多都是處於緊急狀況,我見到曾經歷過武裝衝突、天災和疫症的生還者,精神受到嚴重困擾。因此,無國界醫生提供的醫療人道救援行動不僅要致力保障人們的身體健康,我們的精神健康團隊也在場聆聽、支援和提供護理,使創傷經歷不至於影響他們往後的人生。
可悲的是,有時候無國界醫生不獲准向人們提供這些亟需的援助。無國界醫生在瑙魯向尋求庇護者、難民和當地社群提供心理和精神病服務接近一年後,突然被迫於24小時內撤離該國。在這個偏遠的太平洋島國,我們的救援隊見證到目睹當地的企圖自殺和自殘個案數字驚人,反映被無限期扣押在當地的人們,精神狀況已到達「超乎絕望」的程度。無國界醫生呼籲立即撤離這群無處發聲、失去希望或保護的尋求庇護者和難民,同時要求澳洲政府終止其殘忍、不人道和有辱尊嚴的離岸拘留政策。
我們亦希望為那些飽受痛苦折磨,但卻被主流媒體忽略的人們發聲。今期的封面故事特寫會探討受困於烏克蘭衝突中的老年人、為得到更好未來而屢次嘗試逃離厄立特里亞的兒童和青少年,以及在中非共和國面對性暴力的受害者。要在這些環境下提供精神健康護理並非易事,特別是當暴力和創傷事件持續發生,或是語言和文化障礙使人們不敢尋求協助。我在無國界醫生(香港)負責心理健康聚焦小組的心理健康聯絡主任同事杜顧歷講述了精神健康團隊遇到的挑戰和解決辦法;剛完成救援任務回來的印尼籍醫生Rangi,亦則道出了維持無國界醫生工作人員良好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自今年3月起,被佔領巴勒斯坦被佔領土的加沙幾乎每周都有示威遊行,並遭以色列軍方使用致命的武力驅散。在暴力衝突大幅升溫之際,今期的圖片故事揭露了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集體面對跨代的精神健康危機,以及他們亦逐漸失去應對危機的能力。
令人鼓舞的是,在我們的社會中,普羅大眾逐漸意識到需要關懷那些無形的創傷。無國界醫生請你繼續聆聽身處困苦中的人面對的景況,了解他們的需要。
韋達莎醫生
無國界醫生(香港)署任總幹事
肉體以外的創傷
封面故事
肉體以外的創傷
環顧全球,平均每四個人就有一人於一生中會遭受某種精神問題,不過六成的患者都沒有尋求協助。在暴力、迫害、被迫流徙或天災等因素影響下,這些數字更會大幅上升。
世界各地越來越多人意識到精神健康護理的重要性,但受困於人道危機中的人更需援手。他們特別容易患上抑鬱、焦慮和其他精神疾病。
1998年,無國界醫生正式確認精神健康服務的重要性,將之納入緊急救援工作的一部分。過去十年間,無國界醫生進行了近180萬次精神健康個人輔導和28. 5萬次精神健康小組輔導。去年,無國界醫生展開工作的國家當中,逾七成已將精神健康護理納入醫療服務的主要部分。
陷於衝突、孤獨和創傷之中

「2015年10月,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我家附近不斷發生槍戰和爆炸。我還記得自己躲在後室時,接到可怕的消息。我的鄰居衝進來,說我的兒子被彈片擊傷,傷勢嚴重,最終他在我面前去世,我覺得極度無助。我的兒子死後,我的精神大受打擊,經常顫抖,吃又吃不下。我的兒子是我的好幫手,他是我的所有。」
「我的妹妹叫我離開奧皮娜(Opytne),但這裡是我的家園。我的兒子和丈夫都葬在這裡,我不能離開他們。我情願死在這裡,也不願到其他地方。我一直到無國界醫生的診所醫治精神問題和高血壓。我的兒子去世前,我沒有這些毛病。」
烏克蘭東部歷時四年的衝突,大大改變了當地人的生活。超過100萬人被迫離開家園,那些半荒廢的村落,留下來的大多是獨居老人,他們為著物價上漲,卻沒有足夠退休金而憂心忡忡。許多老年人急需醫療護理以醫治慢性病,並需心理支援以協助他們面對壓力和孤獨的情緒。無國界醫生在頓涅茨克28個地點進行流動診所,提供基本醫療護理和精神健康輔導。救援隊亦向當地的醫療設施提供藥物和設備,並向仍在衝突地區居住或工作的教師和公營醫療設施的醫護人員,提供精神健康支援培訓。

危險旅程的痛苦記憶

伊弗雷姆第一次離開厄立特里亞時,只有14歲。跟其他人一樣,他嘗試去到利比亞,卻被抓住、囚禁和虐打。其後他被遣返回厄立特里亞,被關閉在軍事監獄裡。自此之後,他開始感到嚴重的壓力,並不斷做噩夢。他不再進食,又孤立自己。最終,軍方致電給他的母親。
經過多番嘗試,三年之後,伊弗雷姆終於成功到達埃塞俄比亞。他帶著小量隨身物品,卻背負著過去多年因酷刑、暴力和虐待導致的焦慮和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當我媽媽察覺我不妥時,她帶我到聖水待了七天,那是我們醫治精神健康問題的傳統方法,但我的症狀持續。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如何再逃走。兩星期後,我試圖再次越過邊境到埃塞俄比亞……直至最近,我仍會做噩夢,睡不好,總是覺得很憤怒。」
在埃塞俄比亞北部,無國界醫生在希撒難民營的精神健康中心提供輔導、住院和門診精神科護理,以及各種治療性活動,包括治療性討論和心理教育。難民營內約四成人為兒童,當中一半人獨自流徙,或與家人失開。
支離破碎的人命

*此為化名,以保護受訪者身份
「我的丈夫被武裝分子殺死,我則被俘虜了。在武裝分子的營地裡,那些男人強姦了我。我被關了在那裡數天,失去了我其中一個孩子。最後,我成功把另一個孩子送出營外,自己也逃走了……跟輔導員聊了一段時間後,我感覺好了一點。但這並不容易,一點也不容易。」
塔蒂亞娜憶述她的遭遇時,聲音小得難以被聽到。她的經歷並非個別事件,在中非共和國,性暴力一直以來被廣泛用作戰爭的武器,民眾目前正面對另一輪暴力升級。無國界醫生於今年首六個月在全國各地醫治了1,914名性暴力受害者。在首都班吉,無國界醫生開設了專門醫治性暴力受害者的診所。自這間診所於2017年12月正式啟用後,約有近800名人接受了治療,大部分人為女性,當中四分之一人為18 歲以下。醫療隊不僅協助性暴力受害者預防性病、醫治他們被侵犯時引致的傷勢或婦科併發症,心理學家亦嘗試減輕受害人被侵犯所承受的心理影響,並紓緩他們的症狀。

杜顧歷:精神健康護理就是信任

肉體損傷可以癒合,但精神創傷則難以治癒,病人需要長時間接受治療和坦承吐露心事。對於無國界醫生心理學家杜顧歷(Guleed Dualeh)而言,精神健康支援是關乎溝通,而溝通是建基於信任。
與無國界醫生其他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和輔導員一樣,杜顧歷向病人提供支援時,必須克服各種障礙和限制。2015年,他在緬甸執行前線救援任務,在一名翻譯員的協助下為當地流離失所的羅興亞人提供心理急救。「一名看上去相當苦惱的婦女向翻譯員講出自己的處境和經歷,她用當地語言說了約15分鐘,但最後翻譯員只以一句說話總結:『她的狀態很差。』顯然,那位婦女所說的遠多於此,但似乎翻譯員不太願意複述她所說的話。值得留意的是,翻譯員在翻譯別人的故事時,有機會遭受替代性創傷,因為翻譯員與病人來自同一個地方,翻譯過程中可能會喚起他自己的經歷。」
與病人建立互信是另一項挑戰。「他們不一定會信任心理學家,也不會每個月向一張新的面孔敞開心扉,所以無國界醫生派心理學家到前線項目,他們的任務為期最少6個月,除非心理學家是到當地進行評估,不用直接接觸病人;無國界醫生亦會在緊急情況下,短期派出心理學家到場提供心理急救。」要將心理學家由陌生人變為可信任的人,關鍵是保持服務的連貫性和肯付出時間。另一個方法是在社區裡招募員工,他們是曾接受或未曾接受正規訓練的輔導員。這些輔導員與病人有著共同的語言、文化背景和經歷,較容易聯繫起來。此外,心理學家必須確保所有輔導員都有被聆聽的機會,關顧團隊每一個人的精神需要。
員工的精神健康是無國界醫生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一環。由於救援人員經常長時間在外、處於高度壓力下工作和處理創傷事件,故此他們需要專業的支援和傾訴的空間。曾三度參與無國界醫生救援任務的杜顧歷,於去年開始擔任無國界醫生(香港)的心理健康聯絡主任。救援人員在執行救援任務的前後,杜顧歷都會為有系統地與他們進行會談。他亦正在建立一個地區性的心理學家網絡,為從亞洲13個地區招募的救援人員提供近距離支援。
巴勒斯坦西岸:被佔領下的精神健康問題
圖片特寫
巴勒斯坦西岸:被佔領下的精神健康問題
自今年3月30日以來,巴勒斯坦被佔領士加沙的暴力衝突大幅升溫,逾5000人受傷。當無國界醫生在加沙醫治的大部分傷者遭槍傷,肢體可能永久殘缺之際,在西岸的人們需繼續承受被以色列佔領,以及對他們的精神健康所帶來的持久影響。
無國界醫生在巴勒斯坦的項目總管拉莫斯說:「我們的救援隊竭力支援遭遇暴力事件的人們。這些事件包括親人被拘留、學校和住所被粗暴搜掠、家園被清拆、家人被殺害、在檢查站遭搜身,以及日復日遭佔領者與軍人騷擾。」
西岸城市希伯倫是21.5萬名巴勒斯坦人的家園。無國界醫生自2001年起,在該區進行精神健康支援項目。單是今年,救援隊已向超過6,400人提供個人或小組輔導、心理治療、心理急救或心理教育支援。病人的主要症狀包括焦慮、無法入睡,以及感到悲傷和恐懼。無國界醫生在希伯倫的心理學家蘇波說:「受受精神困擾的人當中,不少是青年人,這對他們成年以後的生活構成影響。在他們這個年紀,需要的是自由,不受約束地到處去,以及可期盼的未來。」
雖然精神健康問題在巴勒斯坦很普遍,但歧視仍然嚴重。因此,令社會意識到精神健康的重要性,以鼓勵人們在有需要時尋求協助是十分關鍵的。
利比里亞:治療嚴重精神病的整體方案
救援冷知識
利比里亞:治療嚴重精神病的整體方案
對無國界醫生而言,治療受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嚴重抑鬱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所困擾的精神病患者,尤其那些生活在低收入國家的人,依然是一個挑戰。無國界醫生現已發展一套整體的護理模式,顯著改善患者的生活質素。
在利比里亞,嚴重精神病患者極難獲得有效的治療,令他們和其家人都痛苦不已。
無國界醫生在利比里亞的精神健康服務經理巴拉說:「無國界醫生的救援隊首次探訪一名32歲的精神病人時,他被鎖起來已有好幾個月。他的家人因為不知道該如何處理他不時出現的暴力行為,在絕望下用鎖鏈把他鎖了起來。」
如果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對症治療,而家裡又沒人能整天看顧,家人不得不使用極端的做法─將病人鎖起來或綁起來,把他們關在家裡,或者送他們去教堂,由其他人禁止他們自由行動。
為改善在利比里亞針對精神疾病和癲癇的治療,無國界醫生發展了以社區為本的模式,治療和護理都在基本醫療診所內提供,這樣精神病患者也可以像其他病人一樣前來求診。經過無國界醫生經驗豐富的精神健康專家的培訓和監督,利比里亞當地的醫生和護士可以用藥,並跟進病況進展以確保病人堅持療程。 巴拉續說:「透過適當的精神狀況評估,諮詢和藥物治療,我們幫助了精神病患者和他們的家人管理患者的病情,他們不再需要使用那些可悲又有害的做法。」
此外,社區衞生人員會主動找出有需要的病人,尤其是那些無法來到診所的人。例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個病徵是患者行動不便,令他們無法自行去覆診。他們亦對自己的病情缺乏理解,即使獲給予藥物,也可能難以依循治療。

癲癇症並不算是精神病的一種,卻能使人變得脆弱無助。無國界醫生的救援隊曾過看一名18歲的青年男子,他患有癲癇症,經常發作,並有發育障礙。因為這個病,他從未上過學。
社區衞生人員發現了這個年輕人,給他的家人介紹了與病情有關的資訊,並把他帶到診所。對癲癇症患者而言,恥辱和污名仍是主要的挑戰,人們有時出於誤解,將這些患者視作威脅。這名年輕人接手過治療,癲癇症不再發作後,社區衞生人員給了他很大支持,幫助學校裡的師生理解他的病情,讓他得以入學。年輕人重新找到了人生目標,他的家人也如釋重負。
無國界醫生自2017年9月開始在利比里亞展開精神健康和癲癇症的治療項目,目前為超過900名患者提供治療。無國界醫生於1990年至2009年間在利比里亞工作,其後於2014年重返該國,應對伊波拉疫情。現時,無國界醫生還在首都蒙羅維亞開設了一間兒童醫院。
「即使不好也不要緊」
救援實錄
「即使不好也不要緊」
南蘇丹自2013年爆發衝突以來,已有240萬名平民逃到國外成為難民,另有200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聯合國在當地為流離失所者設立了6個「保護平民營地」,當中最大的營地設於本提烏,收容了近11.5萬人。
2014年,無國界醫生在本提烏設立了一所有160張病床的醫院,提供不同範疇的服務,包括急症科、成人與兒科住院、營養治療、結核病/愛滋病治療與護理、孕產婦與新生嬰兒科、性暴力受害者護理、外科手術與外展醫療服務。
而我是急症科和營養治療住院部的醫生。
瘧疾季節
我抵達本提烏時正值是瘧疾肆虐的季節,是醫院最忙碌的時段。「保護平民營地」的居住環境很惡劣,增加棲身營內的人們感染瘧疾的風險。
我們的急症室平均每日收治200名病人,有一日人特別多,我們醫治了約700名病人,所有病房都爆滿了,也有一些病情複雜的瘧疾個案。
雖然忙個不停,但我真的很享受在本提烏的救援任務。在南蘇丹的本地同事都非常勤勞,他們從不抱怨,總是盡最大的努力去服務他人。他們為我當翻譯,協助我與病人溝通。

停下步伐
雖然我熱愛這份工作,但必須承認經常處於高度壓力下,會影響前線救援人員的精神健康,這是我們必須正視和處理的問題。
以我為例,每當工作得特別辛苦時,我都會稍作休息。我學會需要幫助時,要誠實面對自己。

我會好好休息、重拾興趣愛好,跟我愛的人聊天,以舒緩壓力。我很幸運,擁有由家人、朋友和無國界醫生組成的強大後盾。我認為重要的是向自己承認,即使不好也不要緊。
很多人都問我,最想念無國界醫生救援任務的什麼部分。我每次的回答都一樣:人。每天工作結束後,我會坐在醫院裡,與同事喝著茶,或跟快將出院的孩子玩耍。在他們的身上,我學到了很多東西。他們令我體會到,與他們所承受的苦難相比,我的煩惱根本微不足道。
Rangi Wirantika Sudrajat是來自印尼的醫生。在過去四年間,她曾四次跟隨無國界醫生,到巴基斯坦和也門等國家參與前線救援任務。她最近剛從南蘇丹完成任務歸來。

愛是良藥
無國界醫生(香港)
愛是良藥
有位無國界醫生的救援人員曾說過,愛有著與藥物一樣的功效,能讓一些病人以驚人的速度康復。這句說話雖然不能以科學驗證,卻在救援前線不少故事中體現得到。
希臘是歐洲流徙危機中許多移民和難民長期滯留的國家,溫泉關一間荒廢的渡假酒店,便成為他們的聚居地,22歲的賽義迪是待在那裡的其中一人,無國界醫生的救援隊在該處提供精神健康服務時認識了她。賽義迪因長年家暴,遭丈夫毆打至遍體鱗傷,甚至面對死亡威脅,迫不得已遺下兩名幼子逃離伊拉克,隻身登上偷渡船。賽義迪說:「要忍痛離開孩子,我至今仍無法釋懷,一想到依然禁不住淚下。」
賽義迪的命運,從在偷渡船上邂逅了26歲的穆罕默德那一刻改寫。穆罕默德因宗教迫害逃離伊拉克,他在船上看見賽義迪孤苦伶仃,已暗下決心要照顧她。賽義迪憶述:「那時,我只是問他借氣泵泵救生衣,根本沒想過其他事。」如今賽義迪已成是穆罕默德的妻子。當年僅14歲的賽義迪,在家人威迫下開始第一段婚姻,最終身心受重創收場。現在她在絕望中找到愛,深信自己找對了人。
經歷,讓人更了解自己需要甚麼樣的愛情。此話在相對穩定富足的香港,亦同樣得到印證。Angus說:「我和太太是大學同班同學,同窗的五年間是很好的朋友。畢業後,我倆各自有一些經歷,其後發覺對方是彼此的生命中最重要和最合適的人。」他與太太拍拖四年後,最終於2017年決定共諧連理。他倆有著相同的職業,相近的價值觀,促使他們在婚禮上作出一個特別的安排──把回禮禮物的預算捐予無國界醫生,並在每位賓客的座位上,擺放支持醫療人道行動的感謝卡。

Angus解釋:「我們都是醫護人員,深知受訓過程很不容易。無國界醫生的救援人員受訓後要累積一定經驗,還要離開穩定的工作,到前線救傷扶危,實在難能可貴。加上在籌備婚禮時,聽到無國界醫生的醫療設施遭到襲擊,就更想支持他們。」對於Angus兩夫婦而言,「幸福」是最不浪費的回禮。「我們留意到很多時候賓客們會忘記帶走小禮物,或因它沒啥用途而留在婚宴會場,既造成浪費,又白費新人一番心思。倒不如直接捐助給有需要的人,分享我們的喜悅和祝福。」
今年首八個月,共有170對新人將婚宴回禮捐贈給無國界醫生,為前線救援人員在世界各地提供獨立的醫療服務,不受種族、宗教、性別或政治因素所左右出一分力。於去年年中結婚的Jennifer,同樣選擇捐贈婚宴回禮。她說:「我們很認同無國界醫生提供救援的原則,以及它幾十年來應對緊急醫療人道危機的不懈努力,所以決定將婚宴回禮捐贈。」
對弱勢社群的關注,讓Jennifer與丈夫於非洲大地邂逅。那時他們不約而同參加了一個旅程,到非洲多國拍攝當地非政府組織的工作。「捐贈婚宴回禮符合我倆的性格,賓客們亦很喜歡。還有甚麼方式比向更有需要的社群分享幸福,更能慶祝結婚這個特別時刻呢?」 新人分享的愛,支持不少危困中的人熬過艱難時刻。正如賽義迪,失去孩子的心靈創傷難以彌補,但在無國界醫生提供的精神健康支援下,她逐步走出陰霾,即使處於困境亦抱持希望建立新家庭。
有興趣捐贈婚宴回禮的準新人,歡迎電郵至fundraising@hongkong.msf.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