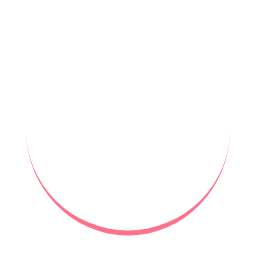加沙戰爭已持續超過一年半,除重大人命傷亡,巴勒斯坦人亦遭受嚴重心理創傷。無國界醫生自這場戰爭爆發以來,一直在當地盡力提供包括外科、物理治療、產科和兒科等護理,以及心理支援。投身人道工作達10年的創傷治療師布魯巴克(Katrin Glatz Brubakk),去年中和今年初隨組織兩度到加沙參與救援工作;今年返回當地時,更在納賽爾醫院(Nasser Hospital)支援戰傷者。她完成工作後,分享在當地的見證,尤其是兒童面對戰爭的心理巨壓:「我聽到孩子驚慌的哭喊,尖叫聲刺進我每個毛孔……」
納賽爾醫院(Nasser Hospital)骨科和燒傷部由無國界醫生協助運作,而布魯巴克就在該部門工作。院肉很多病人都是戰傷兒童,部分需要截肢,而且大多在轟炸中失去家人,有著嚴重心理創傷。布魯巴克面前這位正在哭喊的男孩就是當中一例:「他在爆炸中遭受大範圍燒傷,須接受門診傷口護理,要局部麻醉才可進行。一名護士試圖替他注射麻醉藥,但此舉令男孩感到受威脅且失控。」
那次轟炸中,男孩一家只剩下他與父親倖存,打擊之大令他無法區分針頭的威脅和炸彈的危險。布魯巴克觀察到其反應後,先着護士暫停治療,防止對他造成二次創傷,並請其父靠近輕撫他和與他交談。她花了一段時間令男孩平靜,然後請護士給他服用鎮靜劑,全程其父也陪伴在旁。布魯巴克說:「數周後,其父到診所表達謝意——在戰爭中,他們已對世界的美善喪失信心。在恐懼中體驗到人性關懷,給了他們一絲希望。」
「心靈受創的人需要安穩環境、安全感、可預測的形勢、安全空間以及可靠的社會結構,加沙人無一具備……這十分危險,尤其對兒童來說。」布魯巴克解釋,若兒童長時間極度緊張和恐懼,會對大腦發展不利,因為負責強烈情感印象的杏仁核會持續發展,但負責理性思考及學習的海馬體則發展落後。「我們在戰區展開心理急救的目標,就是為兒童提供無懼時刻,讓他們深呼吸。每個這樣的時刻皆有助防止恐懼變成長期病況。」
布魯巴克提起,曾讓一名年僅3歲的病人瑪麗亞(Maria)好好呼吸、暫時忘憂:「我首次見她時,她極度懼怕我,以及我穿著的無國界醫生白色背心,並開始尖叫。對她而言,醫院一切皆危險,因她將這診所、身體疼痛、轟炸聯繫起來。」
布魯巴克沒有催逼,並用時間換取信任:「我每日只是多次打開她病房的門看看,並以友善語氣說句『你好』。數日後,瑪麗亞變得平靜,那是第一次。此時,我才跟據她的步伐,逐步靠近病床,最後坐在她及她母親旁邊。我從袋中取出我的神奇工具——一瓶泡泡液。瑪麗亞起初的反應很害怕,但後來她鼓起勇氣伸手拿瓶。吹泡泡時,她呼吸加深,注意力轉向美麗無憂的事物。她放鬆起來,那一刻,她感受到快樂,放下恐懼;那一刻,她微笑了。她母親告訴我,這是4個月來的首次。那一刻,我亦感到滿心寬慰。」
布魯巴克和團隊能提供的援助選項很有限,例如難以展開標準的心理療程,也無法對病人說現已安全讓其放心,不過心理急救仍能助他們應對當下;而瑪麗亞的母親看到與女兒的芥蒂消除後,也漸漸理解甚麼有助女兒克服恐懼,開始懂得放鬆。「向親屬提供基本心理知識,也是我與團隊每周舉辦小組的目標,例如我們會解釋,兒童因創傷經歷尿床、拔頭髮或停止說話,是常見反應。」
布魯巴克在納賽爾醫院工作期間,交戰雙方曾短暫落實停火,但當她完成工作回國後,戰火又繼續,醫院更遭火箭襲擊,外科病房嚴重損毀,並造成兩人死亡。心繫同事安危的她,與醫院方面頻繁通訊:「我十分欽佩他們日復日盡心照顧病人,卻不知能否再次見到其孩子活着……有些人給我發訊息,說他們已筋疲力盡,無力再次逃離。我僅有一願:身處其中,支援加沙的同事及兒童。因此,我將於8月再隨無國界醫生返回汗尤尼斯……若屆時我們的醫院仍在。」
無國界醫生仍在支援納賽爾醫院,但以方的撤離令和對醫院員工的行動限制,令其陷入幾近無法繼續正常運作。組織亦於6月10日宣布被迫將該醫院的骨科和燒傷護理工作,轉移至戴爾巴拉赫的前線醫院。